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关于作者:

在他的著作里,马克思对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表述地非常清楚。1 事实上,这样表述已成俗语,重点在于如何理解。我这里说的不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或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这些经典的革命公式点出了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目的(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或一个阶级的自我消亡),但它们并没有描述革命的内容。所以,我想谈一谈马克思在其作品关键处多次重复的,更平实却更具体的另一句俗语,即「剥夺剥夺者」。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在描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写道: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
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巴黎公社时他写道: 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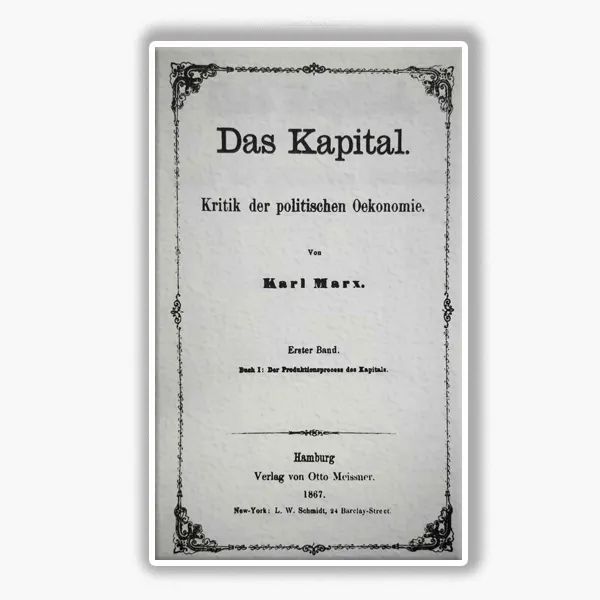
马克思《资本论》丨Wikipedia
马克思甚至把「剥夺剥夺者」与黑格尔著名的「否定之否定」相比。这可能也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最有名的口号,在关于资本主义终结和社会主义到来的通俗读本中被不断引用。但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它在今天是否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以两种方式之一来思考「剥夺」:(a)消极被动的,「原始积累」作为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是历史性(或仍旧持续)过程的一部分;或者(b)积极主动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政党对资产阶级实施的革命举措。但很少有分析将「剥夺剥夺者」置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的论述中,同时又不受决定论或唯意志论影响。我在这里将尝试这样做。 在分析马克思的表达内容之前,我想简要地考虑一下当代法律对「征用」/「剥夺」的理解,以及一些相关的例子。在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我将阐明马克思所述的不同种类的「剥夺」,并着重探讨「剥夺剥夺者」这一概念的的模糊性,即它是否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一种内在的和客观的趋势,亦或是积极地为工人阶级指明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实践形式。我的回答是,它两者都有,这两种内涵看似对立,却非不可调和。解决这种对立关系需要将以阶级剥夺为形式的革命政治斗争建立在资本自我剥夺的客观动态中。这意味着要把这句话的主动的、主观的一面与它的被动的、客观的一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连贯的、中介的观点,即设问成功地剥夺剥夺者需要什么。最后,我通过展示剥夺这一概念如何在今天围绕住房、气候和工作的斗争中被使用,来发展这些思考的一些影响。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为未来搭建蓝图,并避免描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节。然而,我这里是要挑战一种观点,即在马克思没有积极主动越过资本主义的理论6。这不是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终形式是什么样子,而是关于克服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对马克思来说,克服资本主义看起来就像是「剥夺剥夺者」。然而,这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克服资本主义的形式的概念往往会渗透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愿景中。在这个意义上,要把对一种社会形式的否定与对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肯定区分开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呼吁剥夺剥夺者,不仅仅是对某一些东西说不,也是对另一些东西说是。这些最好先说清楚。 
依法征收 / 合法剥夺 从法律上讲,征用是指违背所有者的意愿,通常由国家机关从其手中征收财产的行为,大多是有偿的,名义上亦是为了公共利益。8 征用他人的财产或资产(如房屋、铁路公司或银行),就是单方面但合法地取消其所有权并将其没收。征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征收 (Eminent domain)、国有化、强制收购、社会化等等。例如,征收可能涉及将私人拥有的建筑物的产权和所有权转让给市政府,国有化可能需要将一家能源公司纳入联邦政府的所有权和控制范围,从而将私人财产变成公共财产,而社会化可能涉及将工作场所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让给工人本身。9 大多数国家已经承认了在某些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对国内和国外财产所有者进行征用的有限权利。现在有许多双边投资条约规定了可接受的征用条件。10 这些条件通常规定,征用的明确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它们还要求对被征收的资产给予财产所有者公平和公正的赔偿。然而,这种行为受到民主政府、商业团体、个体业主和富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它违背了自由社会的核心原则,即市场自由、合同法的神圣性和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征用私有财产的权利已经被司法化,并被纳入国内和国际法律,但它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一提到这一行为,就往往会唤起人们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终结的冷战恐慌。 然而,在上个世纪,征用(剥夺)和国有化不鲜见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与能源公司、铁路、煤矿、战时制造业、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电话公司等有关的产业。11 如上所述,法律上的理由是以「公共利益」的概念为前提的,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将私人财产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拿走的理由。当然,「公共利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它的部署取决于当权者的利益。「公共利益」可以指代从提供能源到建造高速公路,到制造武器,到改造社区,到结束垄断,到重新分配财富,到驱逐少数民族的各类行为。20世纪大规模征用(剥夺)的常见例子有:布尔什维克对大地主的剥夺,西班牙内战期间对天主教会的剥夺,纳粹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美国对铁路和煤矿的国有化,拉丁美洲石油公司的国有化,美国在伊朗的企业被剥夺,以及津巴布韦、南非和委内瑞拉的土地征用。 
鉴于这些例子,很明显,征用本身在政治上和规范上是模糊的,这种合法手段可以帮助或伤害弱势社区、富人、少数族裔、政府官员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特定的征用或剥夺是否合理,不能仅仅是一个法律法规和经济影响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即它是否在物质上惠及那些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阶级,并在政治上赋予他们权力。也就是说,某一具体的征用的合法性不能被先验地决定,还须细看财产转移的具体条件,包括谁被征用、谁在征用、征用了什么,以及为了什么目的。 除了这些「直接征用(剥夺)」,还有「间接征用(剥夺)」。也就是说,在不影响财产所有权本身的情况下,使某人的财产或资产变得或多或少趋于毫无价值的行动,例如改变公司存在的金融环境。甚至工业法规也可被视为「间接征用(剥夺)」。事实上,这种「间接征用(剥夺)」的指控已经被跨国公司无数次地用来反对执行环境措施和健康政策。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更积极地将市场从民众的控制中合法地保护起来,12 同时直接征用也变得越来越少,对「间接征用(剥夺)」的恐惧比「直接征用(剥夺)」的恐惧更多地困扰着资产阶级。然而,随着征用住房、能源公司和工作场所这类更激进的社会要求的回归,也许有产者对「狼来了」的恐惧,来的有点太早了。

马克思文本中的剥夺 现在让我们来回看马克思,对他来说,征用或剥夺的含义完全不同。首先,对马克思来说,征用并不以任何法律权利为前提。换句话说,马克思不认为征用被法律合理化了,也不认为其必须被法律合理化。例如,历史上对公共土地的征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在一个根据司法原则授权此种征用的法律框架内发生的——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将征用或剥夺理解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剥夺 (dispossession) 过程的一部分,而不考虑任何一个代理人的任何单一契据的法律效力。第二,征用或剥夺并不要求货币补偿。对土地、财富和劳动力的征用或剥夺没有也不需要进行补偿,如此就可以被认为是征用或剥夺。相反,马克思将征用或剥夺定性为不平等的占有形式,而在资本主义法律关系下,这种占有是在平等交换的幌子下进行的。第三,征用或剥夺不需要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合法地剥夺所有者的所有权,这种想法忽视了私产拥有者或集体代理人是可以迫使国家回溯地承认他们征用或剥夺之行为的。对马克思来说,征用或剥夺的发起者和承受者——剥夺者和被剥夺者——不是简单的国家或个人,而是通过国家和个人调解的不同阶级。简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征用或剥夺是与法律无关的,且可以在无偿的情况下完成,是一个由阶级驱动,长期发生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国家或个人的偶发行为。 在谈到马克思把剥夺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的概念之前,我想首先说明不同形式的征用或剥夺如何被用来区分不同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大多使用「征用」(expropriiert) 的英文同义词。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用「无交换的占有」或 「无等价物的占有」这一更精确的术语来探讨同一概念。13 区分「无交换的占有」的各种对象有助于解读这一短语。在我看来,征用或剥夺的普遍形式是历史性的生产方式或过渡阶段的特征。这里有三个主要对象,分别是是劳动、土地和劳动条件(或基于他人劳动的私有财产)。14 合起来看,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征用或剥夺形式: 1. 通过直接的(经济以外的)胁迫来征用剩余劳动力,这是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如奴隶制或封建主义中对剩余产品的占有的特点;15
2. 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征用土地,这标志着所谓的「原始积累」阶段,并构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关键先决条件,即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以及
3. 通过「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16 从合法自由的工人那里征用无偿劳动,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用剩余价值的特点。 尽管第一种形式的征用在今天仍在发生,但对马克思来说,后两种形式才是关键:作为剥夺 (dispossession) 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征用 (expropriation) 和作为盗窃异化的劳动时间的征用 (expropriation)。所有这三种都是「无等价物的占有」意义上的征用,但只有最后一种具有平等交换的幌子。第二种形式——作为剥夺的征用——确立了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17 这一基本条件是劳动与财产的分离,这既是指直接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条件的分离,也是指生产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18 令人震惊的是,马克思用寻常词汇描述了所有这些征用或剥夺的过程,如「抢劫、掠夺、偷窃、劫掠、篡夺、寄生、强取、消亡、没收、奴役、殖民主义、父权统治、挥霍和放血」19。但是,如果征用和剥夺是如此消极,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根本,那么它如何能成为克服资本主义和创造一个自由人在「公域」生产的社会的途径呢?这就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是否有可能反向征用 (counter-expropriate) 或重新征用 (re-appropriate) 自己的生存条件?如果是这样,这将遵循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即不是废除私有制,而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20 正如资本主义的征用或剥夺否定了直接生产者的个人财产,剥夺剥夺者将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真正的人人有份的个人的所有制——并非通过回到某种前资本主义状态,而是通过集体地重新征用和改造今天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所依据的已经社会化的生产形式。21 然而,鉴于无产者生活在土地、劳动条件,劳动产品,以及他们自己的时间被永久剥夺的条件下,任何将这些物品据为己有的企图,从已经合法剥夺它们的人的角度来看,都会被视为不合法理的征用。然而,这不应该掩盖统治阶级的剥夺和革命的反剥夺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是针对直接生产者阶级进行的,后者则是针对所有者阶级进行的。马克思所要捍卫的正是后一种,以此抵御前一种似乎不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必须有第四种征用,与前三种剥夺的形式不同: 4. 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是生产阶级」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过程,将它们从剥削和奴役的手段转变为「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22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剥夺的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本身促成的,它使资本集中化,劳动社会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束缚。23 也就是说,「剥夺剥夺者」作为资本规律的一种趋势已经在当前发生,但尚未实现,尚未被无产阶级贯彻到底。要将其贯彻到底并加速资产阶级的灭亡,就需要社会化的劳动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力量来切断资本的通路,并将生产条件据为己有。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工人阶级的反抗」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所形成的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并建立在这些条件之上,换言之: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24 
矛盾的是,任务不是要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真实」——否定基于剥夺异化劳动时间的「阶级所有制」,将其转化为基于社会认可的全体劳动的个人所有制。25 
对全体个人的生产资料的剥夺 在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中(写于1863年至1867年之间),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即对剥夺者的剥夺,特别提到了股份公司、信贷系统和合作社。他写道: 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26
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两件事:一方面,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越来越少的个人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这便是一种剥夺的形式),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形式的开创,可以促进从私有制和私有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向在」公域「拥有社会财富的联合生产者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但是,唯有被剥夺的阶级能够完成由资本开始的剥夺,也就是把生产资料从任何个人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后,这过渡才有可能。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将资本主义剥夺的过程扩大到资本阶级本身,以便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再次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人类行使如此巨大的权力。由此产生的在「公域」的由联合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化财富的所有权将不会再现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因为不再有一个单独的所有者阶层可以通过合法剥夺无偿劳动而占有剩余价值。反过来,也不会再有一个形式上自由,经济上却被迫出卖劳动力给雇主,以赚取工资来满足需求的工人阶级,因为不会再有一个垄断生产资料的雇佣阶级,把这些需求以商品的形式卖回给工人以获取利润。相反于工资、价格和利润,个人需求将通过基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社会所有制关系得到满足。 这种被剥夺者对剥夺者者的剥夺,恰恰是通过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形式来实现的,其通过股份公司、信贷系统和合作社 (cooperative factory) ,将所有权和劳动社会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由于这些发展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后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仍然是矛盾的,在形式上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区别,而在实质上却在缓慢地侵蚀着这种区别。马克思继续写道: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7 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生产和占有社会财富的两种过渡形式,这两种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但它们代表了新的「联合的 (associated) 」生产方式的要素: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它通过股票和信贷使私人企业社会化,「消极地解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合作社则通过把联合的工人变成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积极地」解决这种对立。当然,这些「过渡形式」并没有使我们超越我们目前的生产模式。这里可以这样解读,这种形式只有在它们实际摆脱了资本主所有制关系的情况下,才构成替代的「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要素,也就是说,在促进对剥夺者的剥夺,从而废除基于价值、工资劳动和货币的整个交换生产体系的情况下,它们才构成替代的生产方式。此时剥夺不再是在法律意义上取消所有权或移交所有权的征用,而是在革命意义上否定阶级财产的社会和法律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基础是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以及后者被一个占有剩余价值的阶级所拥有,因此,通过剥夺来否定这种分离,无非是人类社会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重回一统,社会存在不再是无意识地通过价格来调解,而是有意识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活动调配。28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变革的潜力已经潜藏在信贷系统中,尽管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马克思认为信贷系统的内部包含着「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30 他这么描述道: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注: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版]。]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1
这段话内涵丰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到信用制突破了生产的束缚,再到物质基础发展导致信用制引发矛盾的暴力的爆发,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自我毁灭倾向。这似乎是一个目的论的故事,信用系统推动资本超越其极限,从而构建新生产模式的基础。但我们在这里应该小心。与其说是决定性的目的论,不如说这展示了一种研究方法,它记录了埋藏在同一社会发展中的众多矛盾的倾向。其中一个趋势是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经济危机、金融诈骗和社会财富被寡头剥夺;另一个趋势是劳动和所有权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和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统治阶级所有制的社会征用(即剥夺剥夺者)的潜力增加。这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于Spannungsverhältnis,一种紧张状态,胜负未决。因此,马克思在结束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剥夺的内在趋势的这段题外话时,对信用制的模糊性质进行了思考: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32
依据马克思以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性剥夺的类型化,以及鉴于对资本主义本身趋向于一种自我剥夺的阐释,我们最终如何解释马克思对剥夺剥夺者的呼吁?马克思既热情地呼吁剥夺剥夺者,同时又冷静地宣布,剥夺者实际上正在被剥夺。这是同一件事吗?关于资本自我剥夺的断言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吗,鉴于资本隐含的长期趋势?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要求剥夺剥夺者?如果这已经在计划之中,那么呼吁剥夺似乎就像呼吁利润率下降一样无用。但马克思并不是决定论的。相反,在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脉络中,马克思对剥夺剥夺者的呼吁不是来自对这种措施的正义性或独立的道德主张,而是来自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发展中的矛盾倾向的描述。 一方面,剥夺剥夺者指的是被剥夺的生产者阶层利用其集体力量夺取劳动工具并将其变成所有人共同拥有的解放工具的政治活动。将这种征用形式形象化的经典方式是通过自发的、普罗大众的自我运动,在运动中,工人参与罢工、占领、接管工作场所、产业链和街区,形成委员会或公社,为所有生产和再生产者的利益而自我管理他们新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例如德国1918-1919年)。但是,要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转变为共同所有制,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剥夺行为;它需要一个能够为新的财产关系的合法性提供保障的政治权威,以及一个能够协调所有人使用新剥夺而来的共同财产的经济组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把一个被剥夺的工厂的新的经济属性,那么由工人委员会拥有和经营的工厂有什么用呢?此外,经济条件是否必须足够「成熟」,才能使这种剥夺具有任何吸引力?如何通过在剥夺中做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出自马克思经济著作的名言进行另一种更谨慎的解读。为了将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趋势中,马克思不仅从革命主体的角度,而且从客体的角度,将「剥夺剥夺者」理论化。 
因此,另一方面,剥夺剥夺者描述了一种无意识的经济趋势,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 「目的」:由越来越少的个人占有社会总财富,最终,无人占有。从「越来越少的个人」到 「完全没有人」的过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不就是一个抽象的飞跃吗?虽然听起来很抽象,但这显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说法,如上文所引。其观点是,资本主义通过各种过渡形式(合作社、股份公司、信贷系统等)使劳动和所有权日益社会化,从而使内在的趋势走向完全消除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这最终将是更有效、更有活力和更合理的生产模式。这就是对生产资料渐进社会化的剥夺,这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社会主义者,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所捍卫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有些行业被认为比其他行业更「成熟」,可以进行这种剥夺,比如煤矿或银行业,因为将其作为公共财产进行合理管理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根据这种观点,对剥夺者的剥夺已经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内部动力发生,以新的形式将劳动和所有权社会化,而这个过程必须被允许发展,直到新的经济组织准备好冲破其法律上仍不完善的外壳。虽然今天有些人可能仍在为这一想法辩护,但要相信相信资本主义垄断企业会合乎理性地将自己剥夺,成为共同财产,以此变得更有效率和更理性的生产力,无疑是痴人说梦。等待剥夺者剥夺自己的可能性似乎和等待地球自我冷却一样低。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剥夺剥夺者」的纯客观主义或纯主观主义的解释都没有真正意义。这句话敲响了黑格尔的钟声,这并不是巧合,因为其模糊性的关键在于对主体和客体之间。 鉴于这句话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政治的、自愿的、革命的、自发的、暴力的和非法的,另一种是经济的、客观的、改革的、渐进的和平的和合法的--有可能把它们协调起来吗?剥夺剥夺者,是指社会对阶级财产的无等价占有,还是指对社会财富的无等价的私人占有?前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式,后者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前者是一种主观意愿的行为,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客观动态。就其本身而言,每一种征用形式都是片面的: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条件使其蓬勃发展,革命的剥夺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政治力量一路推动,资本的渐进式自我剥夺就不可能完成。似乎马克思在他真正赞成的形式上摇摆不定。或者,我认为这更有可能,他在不同时刻对不同读者的不同强调,是为了显示两种形式的剥夺必要的调解,是策略一部分。通过倡导剥夺作为一种革命措施,其形式已经隐含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从其否定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能够将他对剥夺的倡导建立在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和社会变革的政治理论中。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剥夺剥夺者」既是诊断,也是处方,这种处方只有在对现实的具体诊断中才有意义。马克思似乎在说,要彻底剥夺剥夺者,剥夺者本身必须经历自我剥夺,同时,工人阶级可以将这一过程进行到底。(编译者:联想到掘墓人) 
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以两种方式之一来思考「剥夺」:(a)消极被动的,作为「原始积累」这一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是历史性(或仍旧持续)过程的一部分;或者(b)积极主动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政党对资产阶级实施的革命举措。但很少有分析将「剥夺剥夺者」置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的论述中,同时又不受决定论或唯意志论影响。我在这里将尝试这样做。我对马克思这个短语的解释,照顾到了其主动和被动的两面。这种特殊的解释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可以追溯到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辩论,我将在今后的写作中扩展这一主题。 现在,再一次到了重新思考征用/剥夺的时候了,它既是一种法律措施,也是一种解放的政治策略。即使只是提出征用的想法,也能为集体变革开辟以前未曾想象过的视野。33 这里的法律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14条和第15条:「征用只允许为了公共利益」(第14条);「为了社会化的目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可以通过确定补偿性质和范围的法律转移为公共所有权或其他形式的公共企业」(第15条)。这场运动在动员数以万计的租户和邻里,推动改变城市中私产所有权和住房之间的常识性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要求社会征用巨型开发商the Deutsche Wohnen 和 Co Enteignen的产权,运动将基本需求在产权方面问题带到了公众面前。这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使发生了,也很少有这个运动所拥有的法律、社会、政治和经济支持。当然,马克思关于剥夺的论述并不是要从富人那里合法地没收房屋,按市场价格对业主进行补偿,然后将产权移交给国家(尽管恩格斯赞成通过征用来解决住房危机)34。马克思要由生产者本身重新夺回生产条件,使他们能够摆脱对剥削他们的人的财产的依赖。然而,住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也是工人必须支付的巨大生存成本。因此,征用住房,部分地将工人从老板、业主和房东——简言之,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35 为了公共利益而征用财产是不错,但其他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关于征用的论点延伸到多远?德国基本法列出了三个社会化的对象: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那么,为什么不从这些开始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征用土地中的私有财产,让所有人都能免费获得住房?35 为什么不征用私有的自然资源,停止燃烧化石燃料?还有,为什么不征用生产资料,停止为了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最后,让我给出征用/剥夺一切的三个理由。 首先,为了公共利益和基础设施(如道路和电线),但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使一个城市或地区更有利可图(如建造体育场馆),征用/剥夺土地的情况经常发生。其次,为了共同利益而征用土地的权利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规范,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社会。36 一直直到最近,它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必要在法律文件中加以证明。只有在我们的财产关系如此私有化的今天,证明的责任才被放在剥夺者而不是被剥夺者身上。第三,征用可以有效地用于对抗资本主义在住房、环境和工作场所的各种危机。也就是说,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剥夺大房东,停止榨取租金,开始为每个人免费提供住房这是有道理的。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和停止燃烧化石燃料,从投资者手中剥夺能源公司并开始使经济去碳化成为可能。为了重建工人权力,从企业主那里剥夺工作场所,开始为需要而共同生产,这也许不是一个坏主意。
然而,征用私有财产仅仅是第一步。改变一个实例中的所有权结构本身并不改变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因为如果价值和交换关系仍然是社会活动的中介,那么没有理由说征用的房屋、能源公司或工作场所会比私有化模式下有更少剥削、更少异化或对人类和地球更有利。至少现在还不是。正如奥托·诺伊拉特 (Otto Neurath) 在1920年,在工人要求社会化之后,德国的一些产业被国有化,写道:「但是,他们烧的是国有煤而不是私人企业开采的煤,他们的玉米施的是国有钾肥而不是私人企业钾肥,这对他们有什么帮助?」37 这里的问题是,以国有化形式的征用,或作为所有权从私有到公有的转让,如果没有任何其他变化,除了一个新的老板,什么都不能保证。然而,只有在所有权形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所有权的内容才有可能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例如,在德国,住房、煤炭公司或汽车厂的私人业主,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决定』(《德国民法典》第903条)如何处理财产。无论整个社会的需求如何,对业主来说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要挑战财产对人类生活的权力,需要在某些领域对抗这种私人化的权力,这就要提到马克思所述的剥夺剥夺者。这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制定的法律措施,而是一个需要完成的社会过程。例如,征用大型住房公司、化石燃料公司或生产行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是为了达到可以提出有关需求、问责或可持续性议题的关键步骤。没有这一点,人们能做的只是从外部恳求改变。征用意味着不再需要恳请社会财富的个人所有者有更好的行为,而是可以集体永有决定权,以共同决定社会财富的适当使用,无论是住房、能源、技术等方面。这本身并不能保证会有更好的变化,但至少开启了想象空间。 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所有权的形式——从私人到公共或共同——而是所有权的内容本身。将财产的功能从分离转向团结,从利润转向需求,从交换转向使用,从提取转向可再生,从剥削转向关怀,这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在马克思或法律中找到的,而是在今天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社会斗争的内容中找到的——无论是好是坏。/ 1 I am grateful to Rob Hunter, John Clegg,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and the Legal Form editorial collective for their feedback. Previous versions of this paper were presented at HM 2019 and Legal Form 2020. 2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1867]), 929 (emphasis 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3 Karl Marx, The Civil mine).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War in France [1871], MECW 22: 335 (emphasis mine).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4 Marx, Capital I, 929.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5 这种视角受到社会主义者、社民党人、共产主义者和工业家在1918年德国革命后辩论“社会化”的复杂方式的启发,我将在未来的工作中扩展这一主题。
译者注:德国革命相关阅读,详见马库:《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1917—1923年德国革命》
6 关于马克思对克服资本主义的探讨可参考, see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2012.
7 关于这种否定与肯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可参见, Jacob Blumenfeld, “Lifting the Ban”, Brooklyn Rail, 2021.
8‘在英语中,征用/剥夺(expropriation)一词的原意是指不对等地占有不动产的所有权,因此是指将人之于土地的分离、迁移和异化。更广泛地说,征用是指 “剥夺(dispossess)(一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或权利。该术语还具有没收和抢劫等更广泛含义。’.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Expropriation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69, 2018.
9 法律意义上的征用可参考:August Reinisch, ‘Expropriation’, in Peter Muchlinks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07; and Alice Ruzza, ‘Expropri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in Rüdiger Wolfrum (ed),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参考 Expropriation–UNCTAD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J. A. M. A. Sluysmans and E. J. L. Waring, ‘Cor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Expropriation Law’, 2016 (2016) European Property Law Journal 142.
11 See, for example, Thomas Hanna, ‘A History of Nation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7–2009’, The Next System Project (4 November 2019).
12 国家对市场的维护可见:Quinn Slobodian,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 详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8]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me-old.htm : ‘这种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假象的掩盖下来占有他人劳动这一基础上的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 ‘现在已经毫不奇怪的是,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为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最彻底的分离’; ‘等价物的交换好象是以个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因此好象把通过劳动的占有,即占有的现实经济过程,同对客体化的 劳动的所有权等同起来了(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 这里表 现为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 承 认 为 生 产 的一般条件,因而也就在 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这样的等价物的交换 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之间 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四十六卷上); ‘(资本)是不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四十六卷下)。
14 Marx, Capital I, MECW 35, 748: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15 对奴隶劳动的剥夺是完全的,而对农民劳动的剥夺是部分的。
16 Marx, Capital I, MECW 35, 736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
Translation modified. 同时可参阅 Søren Mau, ‘“The Mute Compuls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Abstract and Impersonal Power of Capital’,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3 (2021) 3–32.
17Marx, Capital I, MECW 35, 751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18See Marx Capital III, MECW 37, 608: 《资本论》第三卷 第三十七章《导论》.‘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末,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
19 参见Foster and Clark, ‘The Expropriation of Nature’, fn 30.
20 关于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详见Marx, Capital I, MECW 35, 751: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21 Marx, Capital I, MECW 35, 751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22 Marx, Capital I, 929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MECW 22, 335.《法兰西内战》
23 Marx, Capital I, MECW 35, 750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 [..... ]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
24 Marx, Capital I, MECW 35, 750.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25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335. 《法兰西内战》
至于对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施蒂纳式解读可参见: Jacob Blumenfeld, All Things are Nothing to Me: The Unique Philosophy of Max Stirner (New York: Zero Books, 2018).
26 Marx, Capital III, MECW 37, 437 (emphasis mine) . For the German, see MEGA II/4.2,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7, pt. 2, 503-55. 《资本论》第三卷 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27 Marx, Capital III, MECW 37, 438. 《资本论》第三卷 第二十七章
28 共产主义成为人类重归一统的说法可见 Jacques Camatte, ‘The Wandering of Humanity’ [1973], republished in This World We Must Leav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5) 39.
29 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 MECW 6, 497-506. 《共产党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30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497-506. 《共产党宣言》
31 Marx, Capital III, MECW 37, 438-39. 《资本论》第三卷 第二十七章
32 Marx, Capital III, MECW 37, 438-39. 《资本论》第三卷 第二十七章
33 可参考Jacob Blumenfeld, “Expropriate Everything”, Brooklyn Rail 2019. 也可参考, Sabine Nuss, Keine Enteignung ist auch keine Lösung, Berlin: Dietz Verlag, 2019.
34 见Friedrich Engels, The Housing Question [1872], MECW 23, 317-91.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43.htm
35 Marx, Capital III, 910-11《资本论》第三卷 第四十六章《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36 依据Susan Reynolds,几千年来,"为了公共利益的征用"一直是全世界的准则,而不仅是现代的发明。
Susan Reynolds, Before Eminent Domain: Toward a History of Expropriation of Land for the Common Goo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37 Otto Neurath, ‘Total Socialisation’ (1920), in Economic Writings (New York: Kluwer, 2004), p. 375.
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oxford.scieok.cn/post/3262.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翻译
27102 人参与 2022年07月17日 07:03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



